倪云林 山水 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在禅,游于艺,即是在无我相无人相的寂然不动之中,体会天地大化的自然律动,领受本体的虚灵和万物的虚幻。达摩西来,禅宗于晋时流入东土,于唐宋各处着花,盛极一时。禅宗流入之后,与老庄孔孟同时嫁接,催生内丹之法与宋明理学的大兴,使中原道统心法断而复续,功莫大焉。
艺术作为体道之具,一并受禅宗滋养而生出恢弘气象,诗词、书法、绘画、陶瓷、修建诸门类,均于唐宋到达巅峰。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脉搏,从中能准确捕捉到时代的辉煌与病灶。现在禅宗衰落,向道之心久废,艺术也随之散乱一片,沦为各种花式技法的堆砌和炫耀,却难以掩盖内在的苍白和贫乏。
可以说,不通禅则不能入中国古典艺术的门径。在禅宗滋生的艺术脉流中,倪云林和八大山人是从无争议的大师,像两座孤高的山峰,奇云缭绕,怪雾横生,不停吸引着厥后者的注视和聆听。
倪云林 枯木幽篁图轴幻观云林子曾有诗云:“此身已悟幻泡影,净性元如日月灯。衣里系珠非外得,波间有筏引人登。” 云林与黄公望一样,毕生以修道为主业,书画只是茶余之事。
对修道人来说,色受想行识,本质乃是幻妄。山河大地皆如梦幻空花,无从把捉,不外是虚妄的眼识生出的翳病而已。翳病若除,诸幻自消,方悟妙明真心本有,非假外求。
是以云林笔下山木水石,恍若处于如幻三昧中所观照到的世界,水非水,石非石,一切都随着我相的消隐徐徐冰释。《楞严经》形貌破除色阴后的境界:“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名色阴尽。是人则能逾越劫浊。

观其所由,结实妄想以为其本。”云林笔下景物,好像处在色阴将破未破的边际,流光模糊,亦真亦幻,观幻入空,生出无穷的寂静,恒久的喜乐。晚期云林山水中常有小亭,但亭中空无一人,好像做梦人抽身离去后的梦乡。
这无疑是对凡间梦中人的一记棒喝:如果连做梦的人都是虚构,梦中山水亭石又何以自立?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云:“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一如体玄,兀尔忘缘。
万法奇观,归复自然。”将做梦人与梦乡一齐撤去,悬崖撒手,绝后再苏,方得自在,禅宗的一切手段皆为这一最终目的而施设。觉悟到万法齐等,原本空无自性,才算返回了大道的怀抱,并由今生出无穷妙用。倪云林 渔庄秋霁图轴云林画中,不仅色有的空间正在破灭、消逝,时间也随河水一起停止了流动。
禅宗用河流比喻习气种子的川流,所谓“阿陀那识甚深细,习气种子如瀑流”。证悟实相的人,由念头习气的仆从翻身做了主人,心理时间像云林笔下的河流一样,终于休歇。狂心歇处,即是菩提。
烦恼、渺茫、欲望,连同生死的妄想一起停歇下来,梦中的庞杂、疲惫、惊怖、绝望和奔逃,也一同停歇下来,这正是东方智慧所要告竣的最高目的: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听止于耳,心止于符,于一切内外境界都不复追逐,让心虚灵下来,成为虚而待物的真气。庄子说唯道集虚,老子说为道日损,都是在做虚的光阴。可以说,云林山水的焦点恰在一个“虚”字,它讲明一颗向道的心灵,正在集虚的大道上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似有若无的背影。
此即云林对道的体悟或憧憬,也是隐藏在疏山稀林,水不流花不开的图景中真正的教诲与召唤。八大山人 辛夷 寂照搜狐文化频道,有一篇长文《八大山人,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如此解读《个山小像》上八大自题文字: 49 岁的时候,友人黄安平为朱耷画像,即《个山小像》。
今后,这幅画像长随其身,须臾不离。画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友人和八大山人自己题写的文字,如谶语,如天书,透露出一段段艰辛的心路历程。“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
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八大《自题个山小像》)这首诗透露出八大面临自己画像审视自我时的彷徨无所皈依之感。他发现自己所信奉的释教,无论曹洞宗还是临济宗,都不能让自己的心灵得以休歇,都不是可以依托灵魂之所。奉佛而非佛,奉佛而疑佛,这疲惫不堪、彷徨无依的人是谁?在他看来,自己已经酿成不正经,不僧不道不儒的四不像。“没毛驴,初生兔。
破面门,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目前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
咄!”(八大《自题个山小像》)还是赶忙脱去这一切桎梏,走自己当行的本色之路!其实,出家的二十余年,他心中复仇的火焰一刻也没有停歇,诗中频频表达出“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臣”的宏图雄心,可是,身在空门,效果只能是“梅花画里思思肖,僧人如何如采薇?”(《题古梅图轴三首》)他反思着,自责着,这痛苦不堪的追问让他对自己的生存价值举行了全面的否认,也让他再一次疯癫。疯狂事后,他蓄发还俗,回到自己的家乡。今后,他开始自号“个山驴”——“吾为僧矣,何不以驴名?”(陈鼎《八大山人传》),并刻一“技止此耳”印,明显白白告诉世人,此驴者,笨驴也,黔驴技穷也。另有“驴屋”“驴年”“驴书”“驴汉”“驴屋驴”等。
这自嘲自谑自轻自贱的题款是他对于昨天的彻底否认和对于明天的隐约表示。似这般关公战秦琼,以唯物史观浇八大之块垒者,在今世艺术界并非孤例。此类解读方式又广为流传,可谓一盲导众盲,乾坤暗,山河大地一时黑,显示出文化断层之后令人欲语还休的尴尬。
“曹洞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此偈全是禅家言句,丧家之狗是借郑人形貌孔子语句,类庄子言“荅焉似丧其耦”,实为见道之言。
“生在曹洞”的是人,曹洞临济是法,人法俱亡之后,还剩个什么,试道一句?后面“破面门,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目前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
咄!”与上一则自题言旨大要相当。大慧宗杲问:“藤枯树倒时如何?”其师圆悟克勤答:“相随来也。”宗杲于言下彻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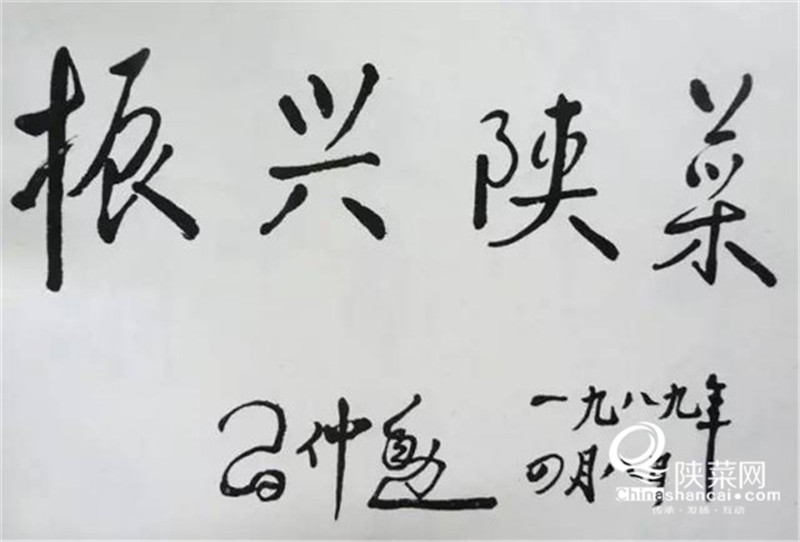
此则公案,正可与八大自题对勘。至于“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臣”,亦非实指。
所谓破山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学习周武王焚鱼告天伐纣,并非是要伐夺取了朱明山河的大清,而是要杀进无明老巢,剿灭心中之贼。后面以驴自喻,亦禅家语,而非自贱。试举几则公案,便一目了然: “从谂与文远论义。远曰:‘请僧人立义。
’师曰:‘我是一头驴。’远曰:‘我是驴胃。’师曰:‘我是驴粪。

’远曰:‘我是粪中虫。’”(《五灯会元》)“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师见云:‘大似一头驴。’普化便作驴鸣。师曰:‘这贼!’”(《临济语录》)“师又问:‘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应底原理?’德曰:‘如驴觑井。
’师曰:‘道则大杀。道只道得八成。’德曰:‘僧人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
’”(《本寂抚州语录》)八大山人 游鱼 无独占偶,常见论者以八大笔下呆鸟怪鱼为证,说明八大心田伤身愤世,对满清愤恨难销云云。参照八大诸多题画诗文可知,真相恰恰相反。八大的呆鸟怪鱼,是溟灭了我相后的自在之身,表相的高冷无情,转达的恰恰是挣脱情识罗网后的虚极静笃。
我与我所俱在无边的静寂喜乐中消融,然后又以梦幻泡影的姿态复生。这正是八大所悟的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八大和云林一样,笔下物象破除了对“相”的牵绊执著,反而获得了更高条理的精神生命:见闻如幻翳,三界若空花。闻复翳根除,尘销觉圆净。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楞严经∙ 二十五圣圆通章》) 八大山人 山水 啐啄禅宗强调当下顿入实相,六祖说,见性之人,言下需见。三祖僧璨大师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赵州说,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确,老僧不在明确里。
禅宗之所以重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于此翻身悟入,乃是因为,言语是心中之贼派出的主力队伍,是颠倒妄见的集中营,是最大的机关陷阱,生生世世囚禁着世人。将语言视为唯一依靠的人,被语言和建基于语言的划分拣择死死地捆绑,直到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死心塌地爱上了语言这个绑匪,频频被撕票仍不悔初心。云林与八大笔下景物,是语言耶?非语言耶?或者如赵州一般,虽像凡人那样开口说话,却“不在明确里”?颠倒的情识,通常以文字相缠绕禁锢我们的头脑。
重重妄念最后包裹成结实的蛋壳,令人求出不得。禅宗师徒传承,向来重视啐啄同时。被囚之雏鸡以嘴吮卵而求出,老母鸡闻吮声,即于其处猛力啄之以助力,最后,师徒协力啄碎坚硬的梦乡,雏鸡得以冲出溷笼,重获自由。
虽曰至道无难,但深陷梦魇者想要挣脱梦乡又谈何容易!如何是诸佛身世处?圆悟答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云林和八大的艺术,或可作为叫醒梦乡的一阵微风,在梦魇者的肩膀上轻轻一推,无量恐慌忙乱由此顿消亦未可知。
云林和八大,也是那只深谙破壳之术的老母鸡,在我们东撞西啐的忙乱中,前来协助一臂之力。或许,他们更大的意义还在于,知道有人在我们的梦外醒着,自己就是对梦魇者最大的鼓舞和激励。本文为姚无咎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民众号“步虚集”。
本文来源:澳门沙金在线平台-www.jmdengbang.com